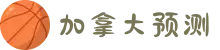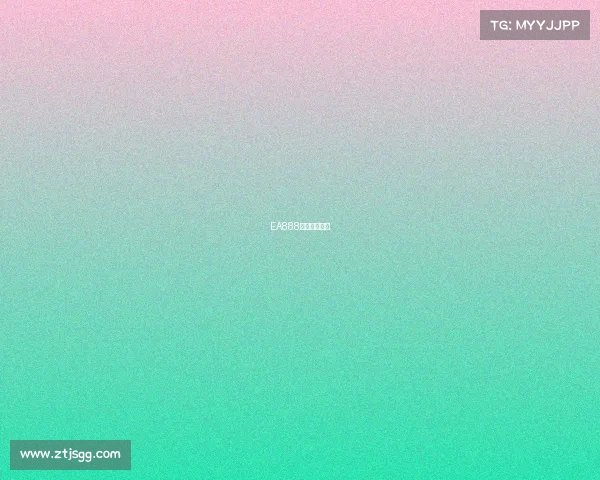土库曼斯坦面积49.1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4个海南岛,人口572万,约为半个海南省。其主体民族为土库曼族,占比95%,主流信仰伊斯兰教(逊尼派),官方语言是土库曼语,俄语为通用语。该国地处中亚西南部,北邻哈萨克斯坦,东接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靠阿富汗,南连伊朗,西濒里海,虽为内陆国,但有港口城市与水上贸易。
西北部临里海处有卡拉博加兹戈尔湾,形似有缺口的大湖,是世界最大的“西湖”。北部和中部多为图兰平原,卡拉库姆沙漠覆盖全国80%面积,西部是巴尔坎山脉,巴尔坎省位于此。首都阿什哈巴德是全国最大城市,位于沙漠与科佩特山脉连接处,人口103万,靠近伊朗。

阿什哈巴德
土库曼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一样面临水问题,主要水源是苏联时期开发的卡拉库姆运河,阿姆河部分流经该国。气候炎热少雨,昼夜温差大,风力强劲,风速可达50米每秒,阿姆河流域40年发生七次龙卷风。
土库曼斯坦自然资源丰富,天然气储量50万亿立方米,石油探明储量2.13亿吨,预期总储量208亿吨,还有芒硝、碘等多种资源。
01
土库曼斯坦建立苏维埃共和国,戈尔巴乔夫进行苏联改革
历史上,此地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遗迹,公元前2000年有稳定人类活动,游牧部落培育出阿哈尔捷金马(汗血宝马),梅尔夫曾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城市,历经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等统治,后被蒙古人摧毁,15世纪形成土库曼族群,最强部落为帖克部落。
19世纪沙俄在此建立港口城市克拉斯诺夫斯克并修建跨里海铁路,发生斯拉夫移民、兴建阿什哈巴德事件。
十月革命后,1920年中亚逐步解放,1924年苏联进行民族划界,土库曼斯坦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过程相对顺利,政治环境相对和谐,但也受苏联政治影响。苏联时代,土库曼斯坦相对安静,后苏联解体,该国也迎来新的发展阶段。
1985年,历史的车轮悄然转向,戈尔巴乔夫登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自此拉开了苏联改革的大幕,整个苏联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开始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动荡与变革。无独有偶,在同一年,一位名叫尼亚佐夫的人物出任土库曼共产党第一书记。

戈尔巴乔夫(中间)
尼亚佐夫于1940年诞生于阿什哈巴德的郊区,其童年命运多舛,父亲在卫国战争中英勇捐躯,随后在1948年,阿什哈巴德遭遇的那场大地震又无情地夺走了他母亲和哥哥的生命。年仅八岁的他,便成为了孤苦伶仃的孤儿,在孤儿院的庇护下艰难成长。
尼亚佐夫并未被命运的重击所打倒,1962年,他加入苏共,凭借着自身的聪慧与勤奋,在学业上崭露头角,被推荐前往莫斯科电力工程学院深造。
但命运似乎又一次跟他开了玩笑,严重的癫痫疾病迫使他无奈退学,踏上了漫长的治病之路。康复之后,他并未放弃求学的梦想,转而前往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即如今的圣彼得堡理工大学)继续追逐知识的脚步。
在求学期间,他还积极投身于基洛夫工厂,体验工人的生活,磨砺自己的意志。最终,在顺利拿到文凭后,他回到了故乡阿什哈巴德,开启了自己的技术官员生涯,从发电厂的基层岗位一路稳步升迁。
1976年,他从苏共中央党校毕业,随后在中央委员会兢兢业业地工作,直至1980年回到家乡,当选阿什哈巴德市委第一书记,1984年又从市委迈入土库曼共产党中央,实现了从政路上的关键跨越。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全国上下寻觅典型案例,土库曼当时的第一书记加普罗夫进入了视野。
加普罗夫在土库曼苏联时代堪称举足轻重的政治家,自1969年担任第一书记以来,大力推动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繁荣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腐败问题,裙带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交换肆意横行。
戈尔巴乔夫借此契机开启政治改革,这便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来填补空缺,经过一番考量,尼亚佐夫进入了他的视线。尼亚佐夫身为孤儿,长期在莫斯科学习与工作,在地方派系中根基较浅,于是在1985年正式出任第一书记。

尼亚佐夫
1990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上宣布结束苏共的一党专政地位,并设立总统职务以取代第一书记的领导职责。这一变革之风也吹到了各个加盟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亦随之进行总统选举,尼亚佐夫成功实现了身份的转换。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头衔的更迭,但实际上,权力的逻辑已悄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往昔第一书记由党任命,如今总统则源于选举授权,这种授权关系的变化直接引发了地方与中央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
02
土库曼斯坦独立,尼亚佐夫进行改革
1991年,苏联解体,土库曼斯坦宣告正式独立。自斯大林划分民族国家以来,土库曼斯坦的政局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这无疑为尼亚佐夫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使其在政治舞台上得以如鱼得水。相较而言,中亚的其他国家在苏联解体之际,局势却动荡不安。
塔吉克斯坦陷入南北对立的内战泥潭,吉尔吉斯斯坦因部落派系的纷争而政变频发,即便是情况稍好的乌兹别克斯坦,也需要总统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进行周旋与斡旋。而土库曼斯坦由于内部冲突较少,总统的权力得以迅速集中,几乎达到了绝对的程度。
看似平稳的局势下,尼亚佐夫亦面临着诸多挑战。
外交层面,苏联解体后,周边国家陷入混乱,尽管土库曼斯坦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但周边的动荡局势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产生波及效应。
例如,其他国家斗争中的失败者可能会非法越境,他国的不稳定因素亦可能煽动国内那些心怀不轨的势力,从而对土库曼斯坦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内政方面,尽管尼亚佐夫大权在握,但他深知自己的权力获取颇具偶然性。起初在苏联大乱前夕被莫斯科任命为第一书记,而后又顺应苏联改制的潮流成为总统,这意味着他人也有可能登上总统之位,其自身的合法性并非坚如磐石。
身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之中,尼亚佐夫自然无法高枕无忧,强烈的安全焦虑感油然而生。对于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而言,保住手中的权力无疑是最基本且至关重要的诉求,毕竟一旦失去权力,所有的政治抱负都将化为泡影。为了缓解权力焦虑,尼亚佐夫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尼亚佐夫
一,进行政治改革。
在行政权方面,苏联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过渡为总理后,他果断废除了总理这一职务,将行政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在立法权上,鉴于苏联解体后选举民选议会成为主流思潮,为了制衡议会,尼亚佐夫设立了人民委员会,并亲自任命大量成员,从而成功夺取议会的立法权。
在司法权领域,他规定所有的法官、检察官必须由总统直接任命,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基本实现了三权集于一身的局面。
二,着力于经济建设。
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作往往能够为政治稳定提供坚实的支撑。苏联解体后,众多国家纷纷采用休克疗法以求快速发展,而尼亚佐夫却反其道而行之,继续强化中央计划经济模式。
在农业方面,保留了农业产量计划配额的工作方法,对于未能完成工作任务的官员予以斥责甚至解雇,通过这种严格的管理方式,土库曼斯坦成功从原棉生产国转型为棉花加工国,并逐步建立起纺织工业。
同时,鉴于土库曼斯坦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尼亚佐夫积极推动资源出口,并利用所得资金投资建设配套的炼油厂和聚乙烯厂,以此提高产业的多样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随着经济的逐步繁荣,尼亚佐夫宣布水、天然气、盐、电等生活必需品全部免费,这一举措极大地收买了老百姓的忠诚,使得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平稳前行了十年之久。
其三,加强社会控制。
尼亚佐夫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社会管控措施,关闭了科学院,吊销了除国有电信公司以外所有的互联网许可证,同时关闭了所有网吧,以此来确保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减少外界信息对国内的干扰与冲击。
其四,推进文化建设。
这一领域堪称尼亚佐夫施政的一大特色,且手段颇为决绝。苏联时期已经为土库曼斯坦的民族文化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在民族主义的塑造上,仍有大量工作亟待完成。民族主义并非天然生成,而是需要通过人为的历史建构与文化塑造来实现。
而对于中亚国家而言,由于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多为游牧民族,文字记录相对匮乏,民族文化建设的难度可想而知。尼亚佐夫为了构建土库曼民族的独特文化与历史认同,大兴土木,利用石油收入将首都阿什哈巴德打造成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大量使用白色大理石,使其成为一座令人瞩目的奇观之城。
2001年,他出版了《鲁赫纳玛》一书,这部堪称民族史诗建构的著作,首先梳理出了土库曼民族的历史脉络,收录了众多重要的文学作品,而后将这些叙事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个人传记之中,进而上升为对全体国民的精神指引,使得尼亚佐夫个人与民族形象紧密相连,成功构建了民族文化与个人情感。
除此之外,尼亚佐夫还推行了一系列与之相辅相成的文化政策,例如改革文字,将土库曼语使用的俄语西里尔字母改为拉丁字母;更改月份名称,赋予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如将十月改为独立月。
2006年,尼亚佐夫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外界曾一度忧心忡忡,担心土库曼斯坦会因权力真空而陷入混乱。然而,土库曼斯坦却延续了以往的稳定态势,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平稳前行。
03
土库曼斯坦在国际上的发展情况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舞台,土库曼斯坦于1995年成功获得联合国的认可,成为“永久中立国”。国旗上增添了联合国会徽中的橄榄枝元素,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巧妙之举。
从中国的视角回溯历史,20世纪80年代,在苏联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出兵阿富汗,引发了阿富汗各地军阀的奋起抵抗,最终苏联撤军,阿富汗却陷入了内战的泥沼,战火纷飞,暴力冲突不断外溢。

土库曼斯坦
中亚地区本就有着深厚的伊斯兰教信仰根基,苏联解体后,政治局势陷入混乱,许多人纷纷借助宗教寻求慰藉和力量,极易受到极端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伊朗作为神权共和国,热衷于向外输出革命理念。
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有着长达804公里的边界线,与伊朗的边界线更是长达1500公里,在这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宣布中立成为了土库曼斯坦的明智之选。
这不仅能够有效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渗透,还能防止国内的反对派与外部势力勾结串联,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客观来讲,奉行中立政策使得土库曼斯坦在90年代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得以独善其身,并且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周边那些棘手的邻国发展外交关系以及经贸合作。
从国内层面看,这符合其自身的发展利益;从国际层面看,这一决策也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pc28预测俄罗斯期望美国能够保持稳定,不希望看到伊斯兰主义在中亚地区进一步扩张;对于美国而言,土库曼斯坦成为中立国,或许为其在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内制造了一些变数;从世界能源市场的角度出发,土库曼斯坦作为拥有丰富油气资源的国家,保持稳定的局势对各方都有益处。

正是得益于中立国的身份,土库曼斯坦收获了诸多利好。
其首都阿什哈巴德类似中亚地区的迪拜,成为石油巨头们频繁造访的城市,也是中亚地区举办国际石油会议和展览最多的城市之一。
约20个重要的国际组织在此设立了常驻机构,其中包括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联合国中亚事务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驻机构、欧洲安全和合作委员会常驻机构等。众多国际大型银行、商务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纷纷在此汇聚。
尽管土库曼斯坦身为中立国,却也并非高枕无忧。
首先是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存在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水资源问题上。
中亚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阿姆河和锡尔河,在苏联时期被分散划分到五个国家。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均依赖阿姆河的水资源,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歧。

阿姆河
此外,苏联在中亚地区修建的许多铁路,在苏联解体后成为了国际线路。例如,以前从土库曼斯坦第二大城市土库曼纳巴德到第三大城市达绍古兹的铁路,其中一段穿越了乌兹别克斯坦。苏联解体后,若无签证,乘客只能下车绕行,给两国的交通和人员往来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土库曼斯坦与阿塞拜疆之间同样存在冲突。
在苏联时期,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关系融洽,两国领导人甚至宣称土库曼和阿塞拜疆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且都位于里海沿岸,都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由于里海油气田的归属权问题,双方关系急转直下,变得极度紧张。在里海的跨界水域中,存在着三个储量可观的油气田。阿塞拜疆陆地面积狭小,陆上石油资源逐渐枯竭,对海上石油的需求极为迫切。而土库曼斯坦虽然陆地油气资源丰富,但在利益面前也绝无让步的道理,两国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2001年,土库曼斯坦甚至关闭了驻阿塞拜疆大使馆,直到尼亚佐夫去世后才重新开馆。这一矛盾一直持续到2018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伊朗五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城市阿克套签署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才基本化解了这一长期存在的争端。
尽管土库曼斯坦是能源大国,但在经济发展上却并不如波斯湾国家那般顺遂。这主要是因为其作为内陆国,石油的出口依赖管道运输。欧美市场是世界能源消费的重要区域,但要将石油卖到这些地区,就必须借助俄罗斯或伊朗的管道,这使得土库曼斯坦在能源出口方面容易受到他国的制约。
因此,苏联解体后,土库曼斯坦积极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协商,试图打造一条名为“TAP”(由四个国家英文首字母组成)的管道项目。
然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三个国家各自存在诸多复杂问题,使得该项目困难重重,目前仅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部分建成,其余部分仍处于停滞状态。最终,土库曼斯坦将目光投向了中国。
1998年,尼亚佐夫访华,希望能够建设一条将石油销往中国的管道。该管道计划经过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巧妙地避开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能源匮乏且局势不稳定的国家。
这一项目推进迅速,2009年完成一期工程,2010年完成二期工程,2014年三期工程投产,2015年总输气量就达到了550亿立方米。到2022年,中土双边贸易额达到111.81亿美元,同比增长52%,其中中方进口额为103.14亿美元,同比增长50.7%,出口额为8.68亿美元,同比增长69.2%。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自2013年起,土库曼斯坦的一些学校开始提供中文教育。不过,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前往土库曼斯坦仍存在一定的难度。
因为土库曼斯坦规定,所有前往该国的人员都必须有邀请人,即便是旅游也不例外,即使中国人可以办理落地签,但邀请人提前办好手续这一环节依然必不可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员的往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期待在未来能够有机会前往这个独特的国家,亲身感受它的魅力与风情。
【文本来源@小王Albert的视频内容】